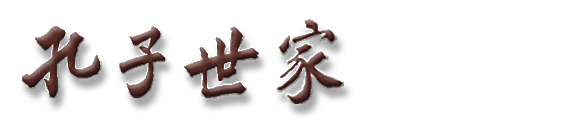从诞生开始,儒学就不单单是形而上的哲学,也是经世致用的日用之学。不过,从两千年前的孔子时代,到两千年后的二十一世纪,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,儒学是否能“俟诸万世而不惑”?或者,另外一种说法是,儒学如何在二十一世纪重新进入公共领域,重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?
在日前举行的儒学刊物《原道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,诸多学者纵论儒学在当下社会意义。
儒学生命力在经世致用
我一直认为儒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,它的生命力应该是经世致用,我是做宋代儒学研究的,我认为宋代儒学很有生命力的原因,就在于它关切两个事情,一个关切世道、一个关切人心,一个是要解决人心的问题、一个是要解决社会秩序等一系列的政治、社会问题。宋明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,发生成东亚儒教文明,我认为也是在这两个方面极大的突破。
今天,要复兴儒学,儒学一定不仅仅是一个只在学校、在课堂上、在书本里学习的时期,而是要和当下社会密切相关,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,儒学要获得生命力,就必须要在这个变化中体现出它的道德价值。
现在儒学日渐受到重视,那么作为儒家本身,究竟应该如何回应这个世界?这看似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也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,但实际上,两千年来,儒学都在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和选择?是“使道行”还是“使道尊”。
在传统时代,两种情况其实一直同时存在,一方面,直接和帝王、和现实打交道,通过和政治的合作来完成行道的庙堂儒学,两千多年都有。但是,这种目标完成的过程,实际上也是道德审判的过程。另外一方面,还有很多的儒者保持儒的独立性,独立地研究儒学,这也有两千多年的传统,就是坚守道德尊严。
从正面意义上来讲,我认为两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换句话来说,儒者如果不和政治系统合作,就是为了保持你的纯正性、保持价值体系的完整性,但结果就是永远变成儒者相互谈论的一个伟大的理想,变成一个学术派别,而这个并不是儒者本身作为他安身立命的完整的价值体系。儒包含道和制,没有那些参与到现实之中,去建立一个合乎儒家理想的社会,儒学就一事无成。同样地,山林儒学在保持道的尊贵性、独立性上的功劳,同样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在今天,儒学要保持强大的生命力,本身应该像历史上一样,有两套系统,一方面儒者的思想和现实、社会产生更多联系,为现实社会服务;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批儒者过冷清的生活,去做学术的研究。
朱汉民(岳麓书院院长)
儒家是时代的引路人
儒家在当下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。因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受西方影响,都不会用中国传统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了,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儒家在这样的趋势中,如何把握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起码我自己认为,我要理直气壮地站在一个儒者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,我们在思考方式上必须把西方式的思考方式中国化,归于道统,就是我们如何去定位自身、如何思考,就是这个时代的行道之道,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第二,具体来说,在这样的一个时代,可能需要做三件事情。一是要推明“治道”。最根本还是要回到经学。二是要创制立法,起码要在知识上创制立法。就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儒家社会治理秩序,究竟是什么样子的?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创造性的思考,就像当初的汉儒、宋儒一样。第三点,我们自己要去行道。一个儒生当然有很广阔的领域可以去行道,比如办书院从事教育,甚至从事社区治理的尝试。但是,对于一个儒家来说,最根本行道的渠道是政治。所以,儒家是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中,你要制君行道,又要以道导君,就不能不去与政治发生某种关系。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,我们对道要有一个自信。
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在权力的对面,我想,可能儒家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是,叫“不拒绝权力,也不恐惧、警惕权力,而是引导权力、改造权力”。但是,究竟在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做?也许去看历史、去看大儒的做法,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。归根到底一句话,还是学问至关重要,这个学问不仅为国家找道,还要为儒者找道。我们都是要通过知识上的努力,同时来寻找这两个道。
秋风(弘道书院院长)
儒者应该谦卑
儒学在公共领域需要做的几个重要课题,第一个就是站在儒家文明的高度上重新刻画中国历史,包括古代史和近代史。比如说,近现代史叙事过去基本上一种是左翼的、一种是右翼的。他们迅速失落,都是因为以政治哲学的立场来看问题。能不能站在儒教文明这样一个高度上,对现代史做出一些褒贬,或者说价值评判?如果有这样的叙事,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。现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,都去面临着按照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史,我觉得应该以儒家的立场去构想一个现代中国,这个做出来以后,一个真正的、跨时代的改变才能启动。
第二个是重新看待儒学和哲学的关系,我们过去传统的哲学系做的,用哲学的方法去阐述儒教的精神,有学者认为这样研究儒学不合适,我想,一个更好更高的看法是,哲学有哲学的用处,应该对哲学的思路给予一个充分肯定,用哲学的方法去阐发儒学精神,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。
最后,要在门外看儒学呢,还是要在门内看儒学?老徘徊在儒门之外不行,你得进来啊。但是,进来有进来的麻烦,徘徊有徘徊的好处。所谓的“进来者”一般都会谈担当,过去都喜欢讲“为天地立心”,我现在对这样的讲法越来越反感。为什么反感呢?实际上,我们在担当的同时一定要谦卑,现在更多缺的是谦卑。历史非常复杂,经典非常深奥,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,才能达到一个综合的理解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事实上,宋明理学认为圣人可以把握天理,这样一个思路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,特别是后来出现的阳明后学,今天领会了一下,那明天就是尧舜了?最后的结果是“尧舜满街走,圣贤不如狗”。就变成了以人的欲望的虚妄代替良知,认为是良知现成,实际都是一些很龌龊的人欲而已。所以,我觉得现在儒学最大的问题,不是没有担当,而是不够谦卑。原来认为是天理天道,现在全部放在人身上,放在人这样一个自然、欲望的禀性上,缺乏对终极者、神圣者的敬畏。所以,我觉得在这方面,可能是我们当下自认要担当儒学的人应该思考的。
唐文明(清华大学教授)
儒者是一种文化的趋向
什么是儒者?儒者与儒者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大,但总体上是一种文化气质在当代社会生活下的人格类型。我觉得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,首先儒者相对于现代化背景下其他文化的人格,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倾向,他遇到问题的时候,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式,就是反躬自省。第二,儒者有一种比较自觉的规范意识。第三,反求诸己和规范意识是相反的,一个是向内的,另一种是向外的尊重现实。二者之间有一种适度的意识,保证前面两个侧面的统一,我觉得从总体文化气质上来说,儒者区别于其他文化人格。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把握。
当然, 具体到个人身上,是非常富于弹性的,针对不同的个体和特点,他对规则的要求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齐白石92岁时候想续弦,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44岁的,他说太老,然后给他引荐了一个22岁的,说这个怎么样?他说这个可以。92岁非要想着娶一个22岁的女孩,如果是别人,大家的观感可能很难接受,但是换到齐白石身上,大家也没有因此觉得他老不正经。这和他外在事业、内在精神达到的高度有关。大家觉得这个老头挺可爱的,92岁了还有这样一个内在的生机盎然。所以,同样是儒者,反求诸己与外在生活的对抗在什么程度下可以被接受,不同的人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标准。
当然儒者不单纯是一个褒义的概念,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趋向。就像刚才说的,自由主义者的道德海拔是很高的,我觉得其实自由主义、保守主义等等,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。儒者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,它不单是一个褒义或者贬义的概念,是一种思维方式、一种自我认同和一个信仰选择。
韩德民(北京语言大学教授)
责任编辑:陈风